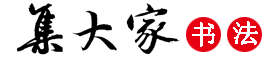第六回
原文:
從來色字最迷人,烈火燒身是慾根。
慧劍若能揮得斷,不為仙佛亦為神。
話說賈道士因看上了胡媚兒,心迷意亂,一夜無眠。不到天明,便起身開了房門,悄悄的踅到樓下打探。只見瘸子在榻上正打齁睡,樓上絕無動靜。回到房中,坐不過,一連出來踅了四五遍,好似螞蟻上了熱鍋蓋,沒跑路投處。跑到廚下,喚起老香公來,教他燒洗臉水,打點早飯。廟中只有一隻報曉公雞,教乜道宰來安排吃罷。乜道已知道士的心事,忙忙的收拾。老香公還在夢裏哩,便道:「阿彌陀佛,留他報曉不好?沒事壞這條性命做甚?」乜道笑道:「師父新學起早,不用報曉了。」
且說婆子和媚兒兩個,在樓上商議道:「我們出外的日子多,行走的路程少,都為著這瘸子帶住了腳,不得快走。這個法官甚好意思,不如把瘸子與他做個徒弟,寄住此間,我們自去。倘然訪得明師,有個住腳處,再來喚他不遲。」到天明,先叫瘸子上樓,對他說了。瘸子正怕走路,恰似給了一個免帖,歡喜無量。
三個商議已定,只聽得樓下咳嗽響,是賈道士的聲音,說道:「婆婆可曾起身?我叫道人送洗臉水上來。」婆子應道:「起動了,待瘸兒自來擔罷。」瘸子下樓擔水,沒拐得四五層梯了,那乜道早已送到。瘸子接上,約莫梳洗了當。賈道士走上樓來作揖問道:「昨夜好睡?」婆子道:「多謝。」這番看媚兒容貌,又與昨日不同。昨日冒雪而來,還帶些風霜之色,今番卻丰姿倍常,真是桃源洞裏登仙女,兜率宮中稔色人。道士看了,沒搔著癢處,恨不得一口水咽他在肚子裏頭。當下殷殷勤勤的問道:「婆婆高壽了?小娘子青春多少?」婆子道:「老媳婦齊頭六十,小女一十九歲了。」道士道:「是四十二歲上生的?」婆子道:「正是。」道士道:「這小哥幾歲?如何損了一足?」婆子道:「村兒二十三歲了。這隻腳是幼時玩耍跌損的。因是他跑走不動,帶遲我們多少腳步。」道士道:「昨日雪下得大了,要銷溶乾淨,也得四五日後,才好走路哩。既是小哥不方便,多住些時也無妨。」婆子道:「老媳婦正有一句不識進退的言語告稟。」道士道:「有話儘說。」婆子道:「老媳婦亡夫,當先原是個火丹道士,與法官同道,只是法術不高。這村兒雖是醜陋,到有些道緣。去年一個全真先生,會麻衣相法,說他是出家之相,要他去做個徒弟,是老媳婦捨不得罷了。今見法官十分憐愛,意欲叫小兒拜在門下,伏侍焚香掃地,不知肯收留否?」道士有心勾搭那小狐精正沒做道理,這一節非親是親,正合其機。便應道:「得小哥在此做個法侶,甚好。只是小道,也有句話,小道從幼父母雙亡,沒個親戚看覷,若蒙不欺,願拜婆婆為乾娘。」婆子道:「老媳婦怎當得起?」兩下謙讓了一回,道士拜了婆子四拜,瘸子也拜了道士四拜,從此瘸子稱道士做師父,道士稱婆子為乾娘。道士又與媚兒重見兩禮道:「今後就是哥妹一家了。」
卻說乜道煮熟了雞,切做兩碗,又整幾色素菜,將早飯擺在樓下。道士同婆子娘兒三口下樓,照先坐定。只因瘸子這番做了徒弟,卻讓道士坐於上首。坐定,道士道:「雪天沒處買東西,只宰得個雞兒,望乾娘賢妹隨意用些。」便揀下碗內好的將筋夾幾塊送上去。婆子道:「老身與小女都是奉齋的,只這村兒用葷,不知法官這等費心,不曾說得。」道士道:「奇怪?賢妹小小年紀,如何吃素?」婆子道:「他是個胎裏素。」道士道:「改日嫁到人家去,好不便當。」婆子道:「那裏嫁什麼人家?他是個有髮的尼姑,時常想著出家哩。」道士想道:「這個又是機緣了。」便道:「出家是好事,只怕出不了時,反為不美。孩兒有個嫡姑,現在淨真庵做主持。乾娘、賢妹花肯離塵學道,逕到那裏去修行。這庵離此處止四十多里,小哥又在這廟中,相去不遠,又好照顧,免得兩下牽掛。」婆子道:「如此甚好。只我媚兒許下西嶽華山聖帝的香願,必要去的。老身伴他去進香過了,轉來時,還到廟中商議。」道士道:「這個卻容易。」
吃過早飯,婆子見道士好情,已是骨肉一家,也不性急趕路了。道士將自己身上半新不舊的道袍,與瘸子穿了,叫眾人稱他做瘸師,又把自房隔壁一個空屋與瘸子做臥室,喚個木匠收拾,做些窗?,卻叫瘸子監工。夜來瘸子也不到樓下來睡了。又整些菜果擺設自家房裏,請乾娘、賢妹,到房中閒坐。說話中間捉個空,就把個眼兒遞與那小狐精。媚兒只是微笑,因此這道士一時越發迷了。有詩為證:
一腔媚意三分笑,雙眼迷魂兩朵花。
只道武陵花下侶,卻忘身是道人家。
道士託熟了兄妹,緊隨著媚兒的腳跟,半步不離,兩個眉來眼去,也覺得情意相通。再過些時,捏手捏腳都來了,只礙著婆子,沒處下手。正是折腳鷺鷥立在沙灘上,眼看鮮魚忍肚飢。一連的過了三日,天已晴得好了,婆子打點作別起身。道士苦留再過一日,婆子被央不過,只得允從。道士回到房中,悶悶而坐,想著只有這一日了,若不用心弄他上手,卻不枉費無益。走來走去,皺眉頭、剔指甲,想了三個時辰,忽然笑將起來道:「有計了。」慌忙在箱籠裏面尋出兩個絕細的綠色梭布,抱到樓下來,對婆子說道:「乾娘、賢妹,這一去不知幾時回轉,揀得兩匹粗布,各做件衫兒穿去,也當個掛念。已喚下裁縫了,明日做完,後日行罷。」婆子道:「重重生受,甚是惶恐。」教媚兒謝了師兄。道士轉身出去,就教乜道村中去喚兩個裁縫,明日侵早要趕件衣服。乜道答應了就去。那乜道一點淫心也不輸與那賈清風,因見那道士手慌腳亂,討不得上手,自己明知不能了,卻也每日留心去覷他的破綻。這番喚裁縫,一定又做什麼把戲,且冷眼看他怎地。
話分兩頭,卻說賈道士那日又白想過了一夜。到得天明,又著乜道去催取裁縫,不多時回覆道:「裁縫已喚到齋堂了。」道士慌忙跑到樓上,教婆子將這布出去,道:「不知合長合短,須乾娘自去看裁,就吩咐他如何樣做,我這村裏的裁縫,沒有高手,若隨他弄去,怕不中意。」婆子真個捧著兩匹布,隨著道士出去。一到齋堂,道士忙覆身轉來,跑到樓下,趁著媚兒獨自一個在那裏,便上前抱住,道:「賢妹,我留心多時了,乘此機會,快快救我性命則個。」媚兒道:「青天白日,羞人答答的,這怎使得!我娘就進來了。」道士道:「你娘處分裁縫,還有好一會。一刻千金,望賢妹作成做哥的罷,休要作難。」便偎著臉去做嘴,媚兒也把舌尖兒度去,叫道:「親哥,做妹子的也不是無情,怎奈不得方便,日間斷使不得。今晚下半夜,母親睡著,我悄悄下樓來,在這榻上與你相會,切
莫失信。」道士便跪下去磕個頭道:「若得賢妹如此,此恩生死不忘。」
說猶未了,只見老香公叫聲:「賈師父!前面老媽媽問你討線哩。」道士慌忙答應,又叮囑媚兒道:「適才所言,賢妹是必休忘。」道士到自房取線去了。不提防乜道正在樓上擔淨桶,聽得賈道士的聲音,悄悄的伏在樓梯邊聽著,雖然兩個說話不甚分明,這個肉麻光景都已瞧在眼裏,料是有個私約了。專等道士出去,便走下樓來將媚兒雙手抱住道;「你與我師父有情我都知道了,不說破你,只要拈個頭兒便罷,井亭上是我起手,少不得謝一謝媒人。」媚兒終是性靈心巧,眉頭一皺計上心來,便道:「你放手,恐怕人來瞧見不好意思,包你有好處。」乜道真個放了手便道:「你怎生發付我去?」媚兒道:「恰才被你家師父纏不過了,教他夜間開著房門,我到半夜到房裏去。你今夜等師父進房去了,悄地先到樓下榻上睡著,我下樓時先與你勾帳,才到他房中去,卻不好。」乜道也磕個頭道:「小娘子果然如此,便是救度生命了。」說罷乜道出去了。媚兒暗笑道:機關泄漏大家不成了,且耍他一耍,教他今夜裏一場沒趣。
卻說婆子吩咐裁縫了當,喚瘸子到樓下,囑咐他道:「你在此間須要學好,我與你妹子明早定是行了。若有些好處,便來挈帶來,休只貪圖酒食,討人厭賤,下次做娘的到此處也沒光彩。」當日道士又來陪吃晚飯,兩個裁縫趕完衣服了,送了進來。道士又向婆子道:「乾娘明日准行了,也不須十分早起,用些早飯了去。」婆子道:「多感厚意,來朝總謝。」
道士有了媚兒的私約,十分快活,回到房中煖起一壺好酒,自家吃得三分醉意,且坐在醉翁?上打個盹,養些精神到下半夜去行事,卻說乜道收拾完了,捉個空先踅在天井裏芭蕉樹下蹲倒。窺見道士房門已閉,娘女兩個也上樓去了,便悄悄地走在榻下眠著,只等樓上的消息,等了半個時辰不覺睡去。這裏道士打了一回盹,不知早晚,只恐失了期約,急急的將雙手抬著著房門輕輕扯開,做個鶴步空庭,一腳一腳的趕步兒走去。到得榻邊將手向榻上摸時,知有個人在榻上睡倒,心裏想道:「這冤家果然有情,已先在此等了。慌忙脫了鞋兒,倒身做一頭睡去。那乜道被他驚醒,也只想道這小娘子不失信,果然來了。兩個並不說話,抱著先做了個甜嘴,只聽得道士低位問道:「你是那個?」乜道已認得是道士聲音,便應道:「師父是我。」道士也認得是乜道了,他如何也在這裏,一定這賊精曉得了些風聲,在此打斷我的好事。於是各自不好意思起來,各自去睡了。這道士分明做了一個魘夢,自己也不信有這事。那時到放下了心腸,一覺睡去。看看天曉,眾人多起身了,道士看看乜道只管笑,乜道看著道士也只管笑。那小狐精看著道士和乜道也只管笑。正是:今日相逢無一語,想來都是會中人。
那道士雖然夜來失望,還想他西嶽進香轉回,尚有相會之日,這個相思擔兒便不肯拋下。當時叫乜道安排酒飯,陪他娘兒吃了。婆子把新做的兩件衫與媚兒各穿了一件,收拾起程。又囑咐瘸子幾句,教他耐心。瘸子答應道:「我都曉得。」道士和瘸子送出廟門,婆子又殷勤稱謝。道士道:「乾娘轉來是必到我廟裏來看看小哥。孩兒明日便寄信到淨真庵姑娘那裏去,倘或發心修行時節,無如那裏清淨。」又對媚兒說道:「賢妹保重,相見有日。」不覺兩眼墮淚,險些兒哭將出來,怕人知覺,便掩著眼急急裏跑進去了。媚兒心裏也自慘然。看官牢記話頭,這左黜自在劍門山下關王廟裏做道士。
再說娘兒兩個離了廟中,望劍閣而進。此時沒有瘸子帶腳,行得較快,一路無話,看看永興地方相近,天色已晚,遠遠望見前面有個林子,約去有十里之程。婆子道:「媚兒,趕到這樹林裏面歇宿,此去西嶽不遠了。」娘兒兩個行不多幾步,忽然對面起一陣大黑風刮得人睜眼不開,立腳不住,那風好狠。正是:
無影無形寒透骨,忽來忽去冷侵膚。
若非地府魔王叫,定是山中鬼怪呼。
風頭過去,只見兩個戎裝力士上前躬身道:「天后有旨,教請聖姑相見。」婆子道:「天后何人?」力士道:「唐朝武則天娘娘也。」婆子道:「則天娘娘棄世已久,如何還在?且與老媳婦素不識面,有何事相喚?」力士道:「娘娘現居此地與聖姑有段因緣,數合相會,便請同行。聖姑姑到彼處自知端的。」婆子心下有些害怕,欲持不去,兩個力士左右的夾幫著,不由你不走。
才動身時,腳不點地,不一時來到一個所在,古木參天,藤蘿滿徑,陰風慘慘,夜氣昏昏。過了兩重牌坊,現出一座大殿宇來。力士不見了,又見兩個宮妝侍女,提著紫紗燈籠,前來引接,道:「娘娘候之久矣。」婆子進殿看時,中間卻虛設個盤龍香案,並無人坐在上面。侍女道:「聖姑姑在此少待。」去不多時便出來道:「天后有旨,請聖姑姑殿後相見。」
婆子際著侍女竟進去,但見珠簾高捲,裏面燈燭輝煌。天后居中坐下,兩旁站著幾個紫衣紗帽的女官,口中喝:「拜!」婆子朝上依喝拜罷,方才平身。天后傳旨賜坐,婆子謙讓道:「天顏之下怎敢大膽。」天后道:「不須過遜,今日之會亦非偶然,朕方欲與卿細論因緣,豈一立談可盡耶。」便叫取錦墩相近,御手相攙而坐。婆子又道:「山野醜陋人所不齒,過蒙娘娘俯召,有何見諭?」天后道:「卿勿以非人自嫌,卿乃孤中之人,朕乃人中之孤,讀駱生檄至今寒心,朕反愧卿耳。」遂吟詩一首,詩曰:
朕本百花王,權閨人間帝,
應運合龍興,作態非孤媚,
國法豈不伸,文人亦可畏,
不敢照青銅,對面還知愧。
又道:「朕那時甚惜駱賓王之才,獻俘時聞有他首級,不忍視之,誰知首級是個假的,駱賓王逃去為僧。從來做官的欺蔽朝廷,都似此類。外人猶以朕為誅戮太甚,公道何在。」又嘆口氣道:「駱生做了和尚,反得昇天,朕今猶滯於幽冥,不思黃巢之亂,百年朽骨,重被污辱,金玉之類發掘一空,致朕今日環佩凋殘,誠羞見卿之面也。」婆子抬頭看時,果然天后頭上挽個朝天髻,絕無簪珥,身上身袍無帶。婆子道:「黃巢草寇無禮,娘娘神靈何不禁之。」天后道:「凡殺運到時,天遣魔王臨世。朕生在唐初,黃巢生在唐末,男女現身不同,為魔一也。朕當權之時,天下誰能禁朕,朕獨能禁黃巢乎?」婆子道:「聞天后在位日,鑄像造塔,廣作佛事,功德不小,為何尚滯於冥途也?」天后道:「凡人先發清淨心,後獲布施福,朕居心不淨,修成魔道,當時享盡女福,單恨不得為男,?佛祈求,無非為此。今因緣將到,已蒙上帝遣作男身矣。」婆子道:「娘娘此番託生富貴,還如舊否?」天后道:「既成魔道,必乘魔運而生,若無權勢,魔力安施?朕前是女身且為帝王,何況男乎?卿女媚兒冥數合為朕妃,即今已託之沖霄處士,卿勿慮也。」婆子道:「娘娘既轉男身,復得稱孤道寡,豈少三宮六院美麗妖嬈,而擇取異類之女乎?」天后道:「卿有所不知。媚兒前身是張六郎,當時稱他貌似蓮花者。朕與六郎恩情不淺,曾私設誓云:生生世世願為夫婦。不幸事與心違,參商至此,今朕為君,彼復得為后,鴛鴦牒已註定,豈可變哉。朕之發跡當在河北,從今二十八年復與卿於貝州相見。卿宜琢磨道術以佐朕命。」婆子道:「吾母子正為求道而來,不知道術在於何處?」天后道:「朕有十六個字,卿可記取,必有應驗,道是:逢楊而止,遇蛋而明,人來尋你,你不尋人。」天后又道:「卿三年之內必有所遇,行住一般不須性急。若得道之後,可往東京度取卿女,雖然改頭換面,卿亦自能認也。天機宜秘,不可輕洩,倘八十翁聞之為禍不小。」婆子問道:「八十翁何人?」天后道:「漢陽王張柬之也。他為五王之首,與朕世世作對,卿宜避之。」
說猶未了,只聽得殿前一片聲吶喊。侍女驚惶傳報道:「漢陽王聞娘娘復有圖王之意,統領大軍十萬,殺將來也。」天后嚇得面色如土,起身向座後便跑。婆子道:「娘娘挈領老媳婦,一路躲避則個。」心忙腳亂,把錦墩踢倒,撲地絆了一交,驚出一身冷汗,原來臥在一個大墳墓下,殿宇俱無,身邊已不見了媚兒。四下叫喚,全無跡影,正不知那裏去了。哭了一回,想道:「嚴半仙說我女兒有厄,果然有此不明不白之事。」看看天曉,只見墓前荊棘中橫著一片破石,石上鐫著大唐則天皇后神道字樣。婆子道:原來夢中所遊,乃天后幽宮,他吩咐許多言語,一一記得,此事甚奇,我且看這十六個字有何應驗?雖然如此,想起初離土洞時,母子三口,劍門山留下了黜兒,到此又失去了媚兒,單單一身,好不悽慘!既道是行住一般,不宜性急,且到太華山下尋個僻靜處住下幾時,再作道理。因這一節有分教:老狐精再遇一個異人,重生一段奇事。正是
踏破鐵鞋無覓處,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畢竟媚兒何處去了,這聖姑姑有甚人來尋他,且聽下回分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