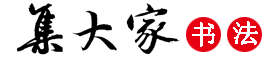第八回
原文:
伊尹空桑說可疑,偃王卵育事尤奇。
書生語怪偏搖首,不道東鄰有蛋兒。
話說慈長老在菜園中埋了小孩子,方欲回身,只見那孩子分開泥土,一個大核桃般的頭兒鑽將出來。慈長老慌了手腳,急將鋤頭打去,用力過了,撲地趺上一交,把鋤頭柄兒也打脫了。爬起來看時,那孩子端端正正坐在雞窠裏面,對著慈長老笑容可掬。慈長老心中不忍,便道:「小廝,你可惜討得個人身,若投在求男求女的富貴人家,夜明珠也賽不過你。如何鑽在蛋殼裏去了?你自走錯了路頭,不干老僧之事。今番聽老僧吩咐別投生路,休得成精作怪,恐嚇老僧。」便把鋤頭柄兒按倒,將雞窠翻上冒,著添些泥土,堆得高高的,又取幾塊亂石壓在上面,料是出不得頭,方才轉身。又想道:「倘或走個狗子進來,爬開石塊,怎麼好?我且把園門關上幾重,這怪物不是悶死也是餓死。」
當下帶轉門兒,搭上鐵鈕,回到房中,取一具留橫的新銅鎖鎖上。吩咐眾僧:「直等我來自開。」這長老生性有些固執,眾僧不知他甚麼意思,也不去問他。
一連過了十來日,慈長老心下終是掛欠。想道:「眼見得這孩子不活了,我且看他一看,終不然鎖斷了門,拋荒了這片園地,菜也不要吃一根。」當下取鑰匙去開了鎖,曳開園門。走到西邊牆角頭看時,只見亂石四散拋開,雞窠兒也翻在一邊,內中不見了小孩子。慈長老吃一驚,四下尋看,只見那小孩子赤條條地坐在一棵楊柳樹下,身上並無傷損。已變做二尺長了,生得清秀,只是不能言語。見慈長老近前,笑嘻嘻的一手扯住他的布衫角兒。慈長老沒奈何,把他盪開,轉身便跑,再也不敢回頭。離了菜園,心頭還突突的跳。暗地想道:「我恁般埋了他,又是甚麼神鬼弄他出來。終不然,一點點小廝,許大力氣自會掙扎。便泥裏鑽出來時,這些石塊如何運得開去?況且十來日裏頭,就長了一尺多,若過二三十年怕不?破天哩!恁般怪事,古今罕有。這禪堂中觀音大士靈籤極準,我且問個吉凶。若是該留下撫養,或者到是個聖僧,不是我們滅得他的。若不該留時,再做商議。」
原來禪堂中供養的,是一尊檀香雕就的觀音大士。案前設個籤筒,有人來求籤,吉凶有驗。慈長老那時也是無計可施,只得取了籤筒,在大士臺前磕頭祝告道:「弟子出家多年,小心持戒,不合潭邊汲水,把個蛋兒攜帶送與鄰家老母雞。誰知抱出個小無賴,埋之不死,餓之還在。忽然一尺二尺,恁般易長易大,來歷甚奇,蹤跡可怪,不是妖魔,定是冤債。若還天遣為僧,留下並無災害,乞賜靈籤上吉,使我不疑不駭,特地祈求,誠心再拜。」口疏已畢,將籤筒向上搖了一回,撲地跳出一根籤來,拾起看時是個第十五籤,果然註個上吉二字。那籤訣上寫道:
風波門外少人知,留得螟蛉只暫時。
來處來時去處去,因緣前定不須疑。
慈長老詳看籤中之語,道:「螟蛉乃是養子,我僧家徒弟便是子孫,這籤中明明許我收留,料也沒事。」當下就喚老道劉狗兒來到禪堂,吩咐道:「不知村裏什麼人家養多了兒子,撇下一個在我家菜園裏。方才我到那邊看見他在楊柳樹下,倒好個小廝,可惜他一條性命。我們僧家不便收養,你可領他在身邊撫育,倘或成人長大,便剃髮為僧,你老人家也有個依靠。」
原來這劉狗兒是本處一個莊戶,家中也有得過活,因年老無子,老婆又死了,別著一口氣,到賠幾兩銀子,進入本寺做個香火。因自己沒兒,平日間見了人家小孩子,便是他的性命。聽得慈長老這話,一腳跑到菜園楊柳樹下,看時,果然好個清秀孩子。連忙抱在懷中,把布衫角兒兜著,剛轉身到門口,只見慈長老也走將來了。慈長老見老道抱著孩子,心下倒也歡喜,對他道:「你抱進自己房裏去,我就來。」老道忙忙的去了。慈長老拽轉園門,取下這副銅鎖帶回屋中,便向?邊衣架上揀一件舊布衫,一條裙子,拿到老道臥房裏來,把與他包裹孩子。老道道:「舊衣舊裳倒也有幾件在這罷了。還存得幾尺藍布,恰好與與他縫個衫兒穿著。只是沒討乳食處,怕餓壞了。」慈長老道:「乳食那裏便當,早晚只泡些糕湯餵他。若是他該做你兒子,自然有命活得。倘然沒命,也沒奈何,強如撇他在菜園,活活的餓死。舉心動念天地皆知,你老人家肯收養他時,也是一點陰騭,神明也必然護佑。我先前在觀音大士前求下一籤,是個上吉,明日長成喚他叫做吉兒罷。」老道道:「卻喜這小廝歡喜相,只會笑不會哭。從菜園裏抱進來,直到如今也不見則聲。」慈長老道:「是不哭的孩子好養。」
兩個正在講話,只見走進個小沙彌來,看見了小廝,便去報與師父師兄知道。三四個和尚都跑將來,把老道半間臥房?得滿滿的。眾僧問道:「這小廝那裏來的?」慈長老道:「不知是張家兒李家子,撇在我園裏頭。我見他好個小廝,又可惜他一命,因此教老劉收養做個兒子。」只這幾個和尚中,也有好善的,也有惡的。那好善的便道:「阿彌陀佛,養得活時也是我寺中陰騭。」那惡的便道:「誰家肯把自養的孩兒撇卻,一定是沒丈夫的婦女,做下些不明不白的事,生下這小廝,怕人知道,暗暗地拋棄了。我們惹什麼是非,卻去收他。」好善的又道:「莫說這般罪過的話,知他是那家生的。多有年命刑剋爹娘,不肯留下,或是婢妾所生,大娘子妒忌,將來拋卻也不見得。那小廝額上又沒有姓張姓李字樣,有甚是非?」那惡的又道:「撫養他也罷,只是寺院裏房頭哭出小孩兒聲響,外人聞得,不當雅相。」老道道:「這小廝只有這件好處,再不哭一哭兒。」眾僧便不言語。慈長老道:「我出去讓你們在?舖上坐坐,莫要擠倒了這間房子。」說罷走出房去了。眾僧見慈長老有不悅之意,也各自散訖。有詩為證:
收養嬰兒未足奇,半言好事半言非。
信心直道行將去,眾口從來不可齊。
再說老道自收了這小廝,愛如己子。早晚調些糕湯餵他,因不便當,就把些粥飯放他口裏,這小廝也咽下了,又沒病痛。自此老道每日的省粥省飯,養這孩子。過了三五個月,外人都知道寺裏老和尚在菜園裏拾個小孩兒,交與劉狗兒養著,把做個新聞傳說。
東鄰的朱大伯聞著這句話,暗想道:「菜園裏那有什麼孩子拾得?莫不是鵝蛋中抱出來的這個怪物,老和尚沒有安排殺他,撫養在那裏。當時因壞了我一窠雞兒,曾許下賠我幾斗麥,不見把來與我,我如今只說少了麥種,與他借些麥子做種,只當提醒他一般,料他也難回我。順便就去看那孩子是什麼模樣,是那怪物也不是。」
當下朱大伯取個叉袋子,拿著走進寺來。正遇見慈長老在廊下門檻上坐著,手中拈個針兒在那裏縫補那破褊衫。朱大伯道:「老師太,多時不見了。」慈長老一見了朱大伯便想起舊話來,慌忙放下褊衫,起身問訊,道:「老僧許你的麥子還不曾相送。」朱大伯道:「怎說這話。老漢不是來與老師太討債的,自家藏下些做種的舊麥子被一起親眷到我家住下了幾日,都吃去了。少了麥種,只得與老師太借些去。待來年種出麥來,做磨磨送老師太吃。」慈長老道:「我許下了少不得送你的,那論你有麥種沒有麥種。你且回去,一時間我叫人送來。」朱大伯道:「不消送得,老漢帶來有叉袋在這裏。若方便時,老漢自家背去罷。」說罷,便把叉袋子提起與慈長老看。慈長老接得在手,便道:「既如此,你且在這廊下暫住。等老僧進去取來與你。」朱大伯道:「老漢還要尋劉狗兒說句閒話。」慈長老恐怕這老兒進去,看見了小孩兒,口嘴不好,講出什麼是非來,便道:「狗兒在園上鋤地哩。待老僧喚他出來罷。」慈長老左手拿著叉袋,右手去檻上檢起這件補不完的破褊衫也放在左臂上,對裏頭便走。朱大伯劈腳也跟隨進來,慈長老著了急,連忙閉門,已被老兒踹進一隻腳來了。慈長老焦廊燥道:「這裏禪堂僧院,你俗人家沒事也進來做甚。祇不過要幾斗麥子,我又不是不捨得與你,教你廊下等一時兒,你卻不依我說。」朱大伯扯開了口,笑嘻嘻的道:「老漢聞得劉狗兒領下個小廝,要去認一認,看他是胎生卵生。」慈長老聽得卵生二字,說著了筋節,面皮通紅,發作道:「你這老兒也好笑,胎生卵生干你屁事。他自在路上拾來一個小廝,初時便有二尺多長了,難道卵生是大鵬裏頭抱出來的?你瞧他怎的。終不然看中了意,認做你家的孫兒去罷。」便把叉袋子撇在地下,又道:「你既要認你孫兒,我也沒氣力與你擔麥子。」朱大伯見慈長老發怒,便道:「不要我看這小廝便罷了,直得恁地變臉。只怕這野種子,做不成你徒子徒孫哩。」拾起叉袋子,抖一抖抱著,轉身便走。慈長老道:「不要麥子也由得你。難道教老僧央你帶去不成。」冷笑一聲,把門閉了。
朱大伯走出寺門,口裏喃喃的道:「再沒見這樣個出家人,許多年紀,火性兀自不退。便問得這句胎生卵生,也只當取笑,你便著了忙,發出許多說話,好不扯淡。」眾鄰舍見朱大伯氣憤憤的從寺中出來,便問道:「大伯你討什麼東西不肯,直得如此著惱?」朱大伯道:「告訴你也話長哩。去年冬下,這慈長老拿個鵝蛋,說到我家來趁我母雞抱卵,也放做一窠兒抱著。誰知蛋裏,抱出一個六七寸長的小孩子。」鄰舍道:「有這等事!」朱大伯道:「便是說也不信。抱出小孩子還不打緊,把這母雞也死了。這一窠雞卵也都沒用了。我去叫那長老來看,長老道不要說起,是我連累著你,明年麥熟時把些麥子賠你罷。他便把這小怪物連窠兒掇去。我想道不是拋在水裏便是埋在土裏。後來聽得劉狗兒撫養著一個小廝,我疑心是那話兒。今日拿個叉袋去寺裏借些麥種,順便瞧一瞧那小廝是什麼模樣,便不與我瞧也罷了,恁般發惡道干你屁事,又道認做你家孫兒去罷。常言道樹高千丈葉落歸根,這小廝怕養不大。若還長大了,少不得尋根問蒂,怕不認我做外公麼。」眾鄰舍道:「到底是你老人家口穩,有恁樣異事,再不見你提起。既是這老和尚做張做智,你只看出家人分上,耐了些罷。老人家著什麼急事,討這樣閒氣。再過幾日,我們與這老和尚說討些麥子還你,你莫著惱。」大家三言兩語,勸那朱大伯回家去了。有詩為證:
別家閒事切休提,提起之時惹是非,
麥子不還翻鬥氣,何如莫問小孩兒。
再說慈長老因朱大伯這番嘔氣,吩咐老道再莫抱小廝出來。到了週歲,便替他在佛前祝髮。從此廢了吉兒的小名,合寺都喚他做小和尚。只因朱大伯與這些鄰舍說了鵝蛋中抱出來的,三三兩兩傳揚開去,本寺徒弟們都知道了,慈長老也瞞不過了,因此又都喚他做蛋子和尚。
俗語說得好,只愁不養,不愁不長。光陰似箭,這蛋子和尚看看長成一十五歲,怎生模樣,有「西江月」為證:
鮮眼濃眉降準,肥軀八尺多長。生成異相貌堂堂,吐語洪鐘響亮。
葷素一齊不忌,勇力賽過金剛。天教降下蛋中王,不比尋常和尚。
又且資性聰明,諸般經典雖不肯專心誦習,若是教他一遍,流水背誦出來。有人不識起倒,與他賭記,閒時乾自把東道折了。老道將他愛惜自不必說。只這慈長老一條心,也未免偏在他身上。看官,你道為甚的?一來愛他聰明,二來可憐他沒有俗家看覷,三來又一件:這蛋子和尚從幼不忌葷酒,好的是使槍輪棍。雖則寺中沒有這家伙,時常把大門槓子舞上一回,若教他鋤田種地,做一日工抵別人兩日還多。只是性氣不好,觸著他便要廝罵廝打。且喜聽人說話,或是老道和這慈長老隔壁喝一聲時,便氣也不敢呵了。又這幾件上得了住持之心,吃的穿的每加倍的照顧他。那起徒弟徒孫,漸有不平之意,時常合計商量要撚他出去。只是沒個事頭,便有些無禮之處,老道又一口埋怨,下情賠禮。那慈長老又說他是個孤身異種,勸眾僧讓他一分,所以眾僧只得耐他下去。
這蛋子和尚聽得人說是蛋殼裏頭出來的,自家也道怪異,必不是個凡人,要在世上尋件驚天動地的事做一做。眾僧背地裏都叫他是畜生種,又叫他是野和尚,雞兒抱的狗兒養的。心中不美,常想走出寺門,雲遊天下,只為慈長老看待得好,又老道又有父子之恩,所以割捨不下。
忽一日,老道得了一個危症,在?數日。蛋子和尚衣不解帶,看湯看藥的伏侍不痊,嗚呼哀哉死了。蛋子和尚哭了一場,少不得棺木盛殮。又與慈長老討菜園旁邊一塊空地埋葬。慈長老允了,眾僧都有些不像意,唧唧噥噥的說道:「老師太越沒志氣了,一個香火道人也把塊葬地與他。若是死了個和尚,必須造個大塚,傳下兩三代休想剩半畝菜園。終不然把這寺基廢了,都做?墓罷。」慈長老只做耳聾,由他們自言自語,只不則聲。
不一日,擇吉入土。眾僧們也有推傷風的,也有推肚痛的,都不肯來幫助。只一個老和尚把鐃鈸響著送葬。當晚慈長老就收拾蛋子和尚到自房裏去安歇。到第三日,蛋子和尚要做老道的羹飯,念老老道是奉齋的,特地買一塊豆腐,把碗盛著放在廚下。又去買些紙錢,轉來取豆腐時,不知那一個移在燒火的矮凳上,被狗子吃去了。蛋子和尚明知是眾僧們故意如此,又惱又苦,對著灶下哀哀的啼哭。眾僧出來攬事道:「這廚房須不是劉氏門中祠堂孝堂,只管哭甚鳥。早知這塊豆腐恁地值錢時,老師太也該替你看守好才是,如今也不消啼哭,左右不是張狗兒吃,也是李狗兒吃,與你親爺差不多。」
蛋子和尚被眾僧一人一句,數落一場,也不回言。撇卻紙錢,一逕走出寺前,向水潭邊一塊搗衣石上氣忿忿的坐著。想道:「這夥禿驢欺得我也夠了,我如今死了養爹,更沒個親人。老和尚雖好,許多年紀也是風中之燭,朝不保暮。到底是個不好開交,不如半夜三更,放把火燒死了這夥禿驢,方出得這口氣。只長老這條命要留下他的,怎的哄得他出寺門便好。」千思百量,心頭火按納不下。提起拳頭向那搗衣石上只一下,把一邊角兒打個粉碎。
此時東鄰的朱大伯也故了,有個兒子叫做丑漢,大伯死後老和尚念其前情,把五斗麥子去助他喪事,又領著蛋子和尚到他靈前磕頭,所以蛋子和尚與丑漢一向相識來往。這日丑漢正在潭邊低著頭洗菜,只聽得石頭碎響,抬起頭來看時,認得蛋子和尚,問道:「蛋師為甚在這裏試力?」蛋子和尚坐著只不做聲。丑漢道:「你與誰鬥寡氣來?出家人戒的是酒、色、財、氣四件,酒是沒要緊,雖說色財二字,那裏便有什麼婆娘與你偷,錢鈔兒與你撇,只這氣,是日日有的,第一要戒的是他。」蛋子和尚聽了這話,十分氣已降下三分了,便道:「老哥好話,我別無他事,只受這一班禿驢欺侮不過。」丑漢道:「我父親在日,常說你是不落血盆的好人,怎的與他們一般見識。自古道欺一壓二,他先進寺門一日大,你又是單身,除非別處去,不住這寺中罷了。若要同鍋吃飯,後日慈長老去世,還要在他們手裏討針線哩。思前算後,總不如耐氣為上。」說罷提著一把菜,向東去了。
蛋子和尚因這一席話,把放火燒寺的念頭撇開,決意出外遊方。想著慈長老待我甚好,不對他說一句如何使得,又想道:若對他說,一定不放我去,不如硬著心腸,就今日撇開罷了。依先入寺到廚下去看時,紙錢還在碗櫃上,取來就焚在灶前。走到慈長老房中,魆地裏將隨身衣服被單打個包裹放著。等天晚溜出寺門,趁著月光,拽開腳步便走。有詩為證:
不分南北與西東,大步行來去似風,
未必前途都稱意,且離此地是非中。
不說蛋子和尚去後,且說慈長老當晚不見蛋子和尚進房,問著眾僧,都推不知。過了一夜,明日看他的衣服被單都沒有了。心下疑慮,對眾僧道:「你們那一個與小和尚鬥口來,他衣服被單都收拾去了,也不對我說聲,定是賭氣去的。」眾僧那個肯認,都說:「我等並無口角,他立心要遊方久了,只牽掛著劉狗兒,昨日燒些紙錢,是打算出門的意思。」長老不信,吩咐眾僧四下裏尋訪他回來。眾僧口裏答應,那個去尋,只在寺前寺後閒蕩了個把時辰,來回覆道:「沒處尋,想他去得遠了。」吃了早飯,慈長老又催促眾僧分頭再去,自家拄個竹杖,也去村中走了一回。轉到寺前,見這些徒弟徒孫們在水潭邊一行兒擺著,檢些瓦片兒賭打水鼓耍子。慈長老發個喉急道:「我老人家也自家去奔走一遍,虧你後生們看得過,在這寺裏相處幾時,全沒些情分,就不去訪他個下落。」眾僧見慈長老認真,越發不在意,一個道:「不消尋得他,他想著老師太恁地牽掛,決不去遠的。只兩日三日自然來看你。」又一個道:「老師太你便牽掛他,他到不牽掛你。若是他心地好時,不走去了。就去也得對你說一聲。」又一個道:「他將來是一寺之主,我們都沒用的,怎教老師太不掛牽。」又一個道:「他又沒有俗家,原是個淌來僧,老師太有處尋他來,沒處尋他去。又不是我們作中過繼到寺內的,認得他何州何縣,向海底下撈針去。老師太你必定曉得些蹤跡,對我們說知,待我們寫個長帖請書,請他到來便了。」慈長老被眾僧七嘴八舌,氣得開口不得,回到房中落了幾點眼淚。以後也不教眾僧去尋了。每日鎖了房門,自家各處捱問,每遍回來,眾僧背後做手勢裝鬼臉,慈長老只做不知。過了月餘,毫無音耗。慈長老又在觀音大士前求了好幾遍籤,都是不吉話兒,想著起初求的籤訣上說道「螟蛉只暫時」,又道「來處來時去處去」一定是尋不著了。那籤是第十五籤,剛剛撫養到一十五歲,想是天數已定,無可奈何,嘆口氣也只得罷了。正是世上萬般哀苦事,無非死別與生離,天下無有不散的筵席。這段話繳過不提。
再說蛋子和尚出了寺門,立心要遊各處名山,訪個異人,傳個驚天動地的道法。一路化緣前去,到全州湘山光孝寺中,拜了無量壽佛的真身。又往衡州朝見南嶽衡山,把七十二峰、十洞、十五岩、三十八泉、二十五溪都遊個遍。
逢山看山,逢水看水,遇個遊僧道便跟他半月十日,看他沒甚意思,又拋撇了。如此非一。忽一日,同幾個僧家,來這沔陽雲夢山下經過,到個所在,終無人煙,都是亂山。貪著僻靜,只顧走,只見白霧漫漫,前途不辨。心中正在驚疑,內一僧在後面把手招道:「快轉來,走錯路了。」蛋子和尚隨著僧伴轉去,問道:「這是什麼所在?」那僧一頭走,一頭說道:「聞得這裏有個白雲洞,乃白猿神所完。因有天書法術在內,怕人偷去,故興此大霧,以隔終之。」一年之內,只有五月五日午時那一個時辰,猿神上天,霧氣暫時收斂。過了這個時辰,猿神便回,霧氣重遮。內有白玉香爐一座,只香爐中煙起,此乃猿神將歸之驗。曾有個方上道人,趁著這個時辰進去,將到洞口,看見一條石橋甚是危險,情知走不過,只得罷了。這霧氣不知許多里數,若誤走進去,被霧迷了,四面皆無出路,就是走得出時,受了這霧氣在肚裏,不是死也病個夠。這雲夢山共有九百里大,本地還有不曉得白雲洞的。」蛋子和尚聽了,心下想道:「原來真有這個法術在此,我若沒緣時,便與那個有緣。」
過了幾日,撇卻了同行僧伴,獨自逕到雲夢山舊路來,旁著近霧之處,折些枯木,摘些松枝,低低的搭起一個草棚。日裏出外投齋化飯,夜間只在棚中歇息,專等端午日,要到白雲洞中盜取白猿神的天書道法。若是一偷就偷看著了,那一個不去走一遭兒,也不見得天書妙處。正是:
受得苦中苦,方為人上人。
畢竟蛋子和尚怎麼樣去盜法,且聽下回分解。